儿子季承给父亲季羡林带来他更喜欢吃的东西。唐师曾/摄
季承先生家的地板,打扫得光可鉴人,掉上一根头发,也能很清晰地看出来。然而,客人进入时不需换鞋,他自己也不穿拖鞋。
聊着聊着,他突然站起身,自己跑去关客厅的门,解释道:“小孩正在睡觉。”
已快76岁了,举手投足了无岁月的痕迹,即使面对年轻人,他的后背也是半躬的,保持着谦恭的姿态。
围绕着季承,有着太多的争议,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独子,这是一份无可奈何的担当。
是啊,每个人都希望维持住一份伟大的幻觉,这让前贤们难以走下神坛,复归人的身份。
太多的名人之后,不得不向公众趣味低头,因为他们明白,只有这样才能利益更大化,相反,谁回到真相,贸然踏入禁区,谁就会成为公敌。
然而,季承就是季承,他有一份独特的自信,在人生之路上,他从没仰仗过父亲,将来也不想去利用父亲,这给了他勇气。
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留下了诚实的门风,那么,季承先生则将它发扬光大。至少,站在历史与良知面前,他无愧无悔。
“对于季羡林,不能神话和拔高,只有更全面了解,才能真正学到他的好品质。”对于曾经的言行,季承如是解读。
不知道爹有什么用
我生于1935年,出生才3个月,爹就离开我去了北京,准备赴德,这一分别就是11年。
小时候不知道爹有什么用,就偷着问其他同学有没有爹。让我奇怪的是,大家都有爹,为什么我没有。
后来,父亲从德国寄了张照片,母亲挂在墙上,我才知道,我爹长这样。
那时兵荒马乱,母亲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,就去算命,算命先生捂住我眼睛,问能看见什么。当然什么都看不见,一片漆黑,我突然想起家里那张照片了,就说,我看见我爹了。算命的说,这证明他还活着。
那些年很艰难,日本人占了济南,刚开始我叔祖父还有工作,后来他失业了,家计只能靠租房维持。
此外我叔祖母是中医,有一点儿收入,整体上算中等吧。虽然清苦,但过年比现在热闹。
那时必须学日语,我们小孩都不念,把老师给气哭了,她是中国人,没想到大家一起对付她。
后来,父亲从德国回来,我才第一次见到他,彼此很冷漠,这种冷漠贯穿了一生。
过去考**很容易
1952年,我高中毕业,准备(),别人说你爹在北京,你还不去那里考,那样更容易考进北京的**。
听这么说,我就来北京了。其实在哪儿考都一样,当年考**特简单,只要不是班里更差的就没问题,我上中学时成绩很一般,也没复习,考完就完了。
我在前门火车站下车,看见前门楼子,觉得真高啊,还有电车,以前没见过。
父亲当时没宿舍,就住在办公室,我晚上睡沙发上。他带我去东安市场、故宫、北海玩,还喝了豆汁,我喝了一口就给了他,说喝不下去,没想到后来我倒喜欢上这一口了。
我报什么志愿,父亲根本不管,问他也不回答。我第一志愿报航天,第二志愿报俄文,当时文理不分,现在看来有点儿像胡闹了。更后我考上俄文专修学校,即北京外国语**前身,校长是师哲,当时中央急缺俄语人才,对这个学校很重视。
我比我爸入党早
学校在今,即醇王南府,刚开始没宿舍,住了自考大殿,特别冷。
我父亲很少关心我学习,一次问我有什么课,我说了,他叨咕一句“学的是不是太少了”,我们那个学校有速成的味道,除了俄语还是俄语,我**成绩不错,可能我学语言有一点天赋吧。我父亲也会俄语,但对话可能不行,所以没和我说过俄语。
**时我入了党,比我父亲早4年。
那时也不担心工作,只要写“服从分配”就行,你也可以写想去哪里上班,反正也没人看。那时大家以去边疆为荣,所以也没人找门路。我被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,当时中苏正合作原子弹项目,我负责翻译工作。
一到单位,好家伙,我发现那里学语言的有日、德、英、法好几种,此外还有学中文的,一个小有名气的北大诗人也来了,当时原子弹是天字第一号工程,要什么人有什么人,我问诗人干吗来了,他说他也不知道。
前苏联专家不客气
那时前苏联原子能代表团常来,我负责翻译,他们都是院士、学者,很朴素。谈判都是他们团长去,他们闲着没事就喝酒。他们的酒量太吓人了,晚餐喝了好多茅台,回北京饭店还要喝。我早上叫一位专家时,看见屋内一地都是空酒瓶,人就睡在地板上。
还有一位前苏联专家是第一次来中国,他母亲听说中国没吃的,就给他带了一大篮子食物,到了才发现,中国好吃的太多了,就让我把它送给“穷人”。正好,我们这些翻译都是穷人,大家便分了,当然不好告诉他,是我们给拿走了。
代表团团长不喝酒,也禁止专家们贪杯,可他们说“到兄弟家了,还客气什么”。
靠吃虫子才没饿死
中苏交恶后,俄语人才用不着了,单位又不放,让我去做党务。反右时,我算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还好没划成右派。而犯了错误的,有的去了白洋淀,有的去了新疆,有的一辈子没回来。
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,我的定量是28.5斤一个月,没油水,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,那几年大家都生不出小孩。
没吃的,就组织去十三陵挖“豆虫”,就是一种肉虫子,盐腌后油炸,这也不能敞开吃,每人只能给两三条。还有用野菜加黄豆,磨成泥,叫“小豆腐”,其实是喂猪的,大家吃得也挺香。此外,大家发挥科学家的本事,用糠制“人造肉”。再有就是到四季青粪池边挖蛆,做“蛋羹”和面包。
就这样,我算没饿死。我父亲好一点儿,他是一级教授,有补给,此外他是政协委员,可定期到小餐厅吃饭。
我给父亲做批斗牌
“文革”来了,我父亲挨了斗,我是基层干部,不敢去看他,只能趁大家午休时偷着去。正赶上他下午要挨斗,得自己做批斗牌,他心情很糟,便让我做。当时批斗牌是有标准格式的,写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季羡林三个字得倒过来写,并打上红叉子。我能做的就是把吊牌的绳子弄粗点,有的造反派使坏,用铁丝吊牌,批斗的时间长了,勒得脖子特别痛。
那时我父亲一个月才12.5元,又不敢取存款,养不活一家人,是我偷着接济一点。
1969年,我被下放到湖北潜江“五七干校”,很多人觉得再也回不来了,把房子都退了,我心里明白,这长不了。当时说“干校”是“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”,我们不理解,这么好的事,那些没犯错误的人怎么不先去“干校”呢?怎么让我们这些人先通向共产主义?
在“干校”更是运动不断,后来连我们的连长也成了“5·16分子”。林彪事件后,“干校”彻底放羊,大家杀鸡宰鹅,做家具,玩了自考,然后回了北京。
家家都有纠纷
我回来时,父亲负责看大门、收发报纸,利用业余时间,他翻译了《罗摩衍那》。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,大家见面都不敢聊运动方面的话题,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感受如何。
以后国家回到了正轨,我又负责了一段科研开发工作,后调到科研开发公司,退休后在李政道先生的“高等科学技术研究中心”做了10年顾问。
从上世纪90年代起,父亲的名声与日俱增,他自己也挺奇怪,说“我一个学东方语言的,怎么成榜样了”。他从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,总说自己在国学造诣上不如很多人,但这个“帽子”就是摘不下来。
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,难免会看到他在生活中更多的侧面,有争执,其实很正常,哪家没有纠纷呢?这才是真正的季羡林,如果没有这些,反而不知道他是谁了。作为亲属,我们自己都不在乎,不知道外人为什么这么在乎。也许,我对大家给我父亲的评价,有点儿估计不足吧。
【儿子眼中的季羡林】
他也说过一些
未必真实的话
我父亲成了名人后,被大家包围着,很难见到亲人,也听不到外界信息,我感觉他不太舒服。后来我回到他身边,我认为,那是作为父子,我们之间更快慰的时光,他心情很放松,可惜不久就去世了。
他说的话,我不完全同意,他心里其实是明白的,私下也说些不同看法,他说“真话不全说,假话全不说”,其实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他知道是怎么回事,当然做到“假话全不说”也不容易,他也说过一些未必真实的话。
没必要神话季羡林,他身上有好的东西,也有缺点。他爱国,爱家方面打点儿折扣,但也说得过去,此外他很勤奋,在自己的专业上有贡献,这都是优点,应该学习。对他的悼词还算客观,给了3个称呼:语言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。我比较同意,但说他是“社会活动家”,有点溢美了,其实他“活动”什么了?他这一辈子总“被活动”。撰文 陈辉
(北京晨报)
【免费咨询报名电话:010-6801 7975】
咨询报名MSN:xueliedu@hotmail.com
试一试网上报名
咨询报名QQ:
| 1505847972 | 1256358232 | 1363884583 | 1902839745 | 800072298 | 754854002 |
| 中专升大专 | 中专升本科 | 高升专 | 高升本 | 专升本 | 自考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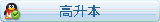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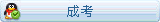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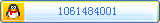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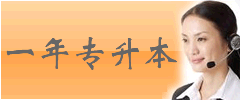
 报名咨询在线MSN:
报名咨询在线MSN: